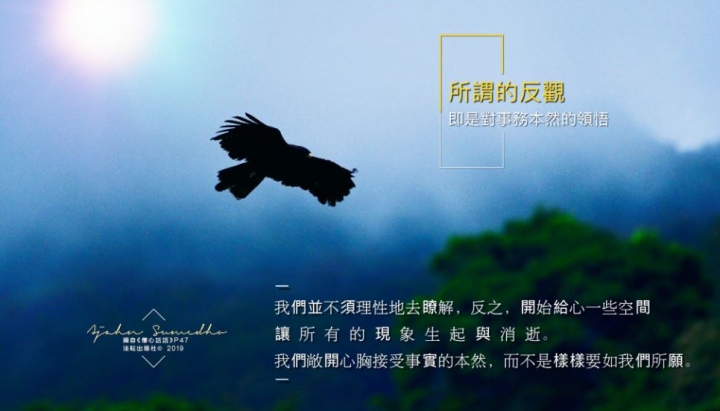心經抉隱 95
遷禪師對忠道者說:「也是海印發光!」就是告訴我們,應緣接物之時,正是真心妙用之處,即海印發光。不要當作起心動念,即落入塵勞。只要隨起隨滅,不住、不停留,正起之時,也不見有心可起,那就是真如的妙用。
若以為不起心動念就是大道,那就錯了。住在黑山背後,就不能成道了。我們要能隨緣起用、應緣接物,一切事情都可以做,這正是我們的大機大用,這就叫做「無為而無不為」。
剛才我們已提到,要破五蘊,看起來不容易。因為它含一百法,單是色蘊就有十一個色法。但只要把道理搞通,破起來也非常容易。如果識得這一切色相都是虛妄不實,都不可得,則不去執著、不計度分別、不妄自議論,那麼,一切色法、一切作為就都是妙用。
所以,《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們不僅要認識到色無自體,係因緣合成而有,色的當體就是空,色和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且還須更進一步認識到,這個空是妙有真空,即我們的真性,不是空無所有的空。這一切色相皆是我們的真性所示現、所造作,皆是自性的影子,皆是我們的化身。那麼,還有什麼可分別執著的呢?這樣,就能空卻色法、破除色蘊了。
舉一反三,色蘊一破,下面的受想行識四蘊,也就隨之紛紛而破了,因為同樣都是虛假不可得的幻影。色相既不可得,還受個什麼呢?無受,想又從何生起呢?依次,行和識也就都不存在了。於是,一破一切破,統統破滅無餘了。因此,《心經》說:「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受想行識四蘊是心法,含受、想兩蘊所攝的五十一個心所法,行蘊所攝的二十四個不相應法,識蘊所攝的八個心王法,共計八十三個心法。五蘊是總法,是一切法的總攝、總體。色蘊既為空性所變現,那麼,受想行識四蘊,亦不外如是之理。即受想行識也是真空妙性所顯之用。真空就是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就是真空。一切攝歸為自心,無點滴餘法存在。一破一切破,八十三個心法,也就消滅無餘了。
--------------------------------------------------------------------------------------------------------
透過禪定中陰,我們在當中尋找什麼?
就是念頭之間的間隙。
這說來容易,但在你心中有任何間隙嗎?
當你想:「間隙是怎麼回事?」就不再有間隙了。
這裡指的是在念頭與念頭之間,生起或發生實相的本然狀態。
我們必須暸解,我們必須「在」那裡。
不是去「想」那個間隙,而是必須「在」那個間隙裡。
這個間隙就是我們的家。
--措尼仁波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