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第一大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高達2940億美元),德國也是特朗普削減貿易赤字行動的主要打擊目標之一。
據2018年的統計數字,美國的貿易逆差高達4550億美元。美國僅對德國的貿易逆差就達580億美元,而且仍在不斷攀升。上一次德美兩國經常賬戶實現平衡還是在1991年。
德國對全球的貿易順差甚至比日本和俄羅斯加在一起還要多,而這兩個國家可以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在貿易順差佔GDP比例方面,德國目前的數字是7.4%,已經比2015年的8.9%略有下降,但仍然大大高於歐盟為歐元區確定的最高6%的標準;德國的貿易順差佔GDP之比更是比中國高出好幾倍。

默克爾與特朗普(資料圖/IC photo)
進口車及零部件也“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特朗普的貿易代表已經指出,美國有兩大問題:中國和進口汽車。這意味着,在與中國打貿易戰之後,美國人就要將矛頭對準進口汽車了。美國商務部認為,“進口的輕型汽車和零部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在德國看來,毫不誇張地說,這樣的觀點是非常令人吃驚的。
把汽車進口稅提高到25%或進口配額問題已在美國被提交討論,而大眾、戴姆勒和寶馬公司的高管們為了避免這一結果,去年12月與特朗普在白宮進行了會談。特朗普已在多個場合對奔馳、寶馬等德國汽車品牌表達了批評態度。上述幾位高管的主要觀點是:他們已在美國建立了多家工廠,僱傭了11.8萬人,在美國生產了75萬輛汽車,而美國從德國進口的汽車僅有47萬輛。
對於德國汽車製造商來說,最大的幫助其實並非來自德國的政治人物(德國政府只會發表空洞的聲明,乾巴巴地解釋自由貿易十分重要,要警惕傷害自由貿易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反而是美國汽車產業自己僱傭了遊說集團對加稅措施表達不滿。
根據美國汽車研究中心2018年的研究結果,25%的汽車整車和汽車零部件進口稅率將導致每輛新車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平均上漲4400美元。其中每輛進口汽車的價格平均上漲6875美元,每輛美國製造的汽車價格平均上漲2270美元,另外在汽車供應和分銷鏈條中,美國還將損失掉70萬個工作崗位。此前特朗普在鋼鐵和鋁製品領域上調關稅的措施已經導致每輛汽車的價格上漲了約400美元。
不過,形勢的發展方向正在變得模糊。
5月15日,據報道特朗普政府計劃延遲半年就是否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征汽車及零部件進口關稅做出決定。很顯然,美國人也覺得與中國和歐盟兩面作戰並不明智。不過,這種做法只是在拖延時間,並非最終的解決方案。
特朗普已經提出要求,他希望歐盟和日本能與美國簽署一份協議,答應在180天內“限制或約束”對美國的汽車整車和零部件出口,否則美國將把進口稅率提高至25%。除非出於國家安全原因(例如英阿馬島戰爭期間兩國貿易中斷),否則這樣的進口配額限制在WTO框架下是不合法的。
其實,美國提出的“進口輕型汽車和零部件對美國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威脅”這一說法是非常牽強的,因為美國給出的理由是:進口汽車和零部件“傷害了美國國內的汽車和零部件製造商,進而傷害了它們在新技術領域投資以開展研發活動的能力”。人們會說,這一切其實就是美國汽車產業缺乏競爭力而已,他們需要國家對其進行保護,這種行為正是WTO的相關條款所反對的,而WTO的那些相關條款正是美國自己在很多年以前推動通過的。
公平地說,德國目前對來自美國的汽車徵收10%的進口稅,而美國對來自德國的汽車僅徵收2.5%的進口稅。德國方面的立場似乎是,為了解決這一稅率失衡問題,雙方都應該把稅率降到零。
其實,沒有德國人害怕美國汽車會佔領德國市場。在德國有一句玩笑話:即便美國人把車賣得再便宜,美國車在德國的銷量也不會有什麼變化。因為美國車並不符合德國人的用車需求,德國人也不欣賞美國人的造車品味。美國車太大、太耗油,而且造車工藝也比較差。很多德國人都把自己想象成舒馬赫一樣的人物,認為自己需要一部能夠在賽道上狂飆的座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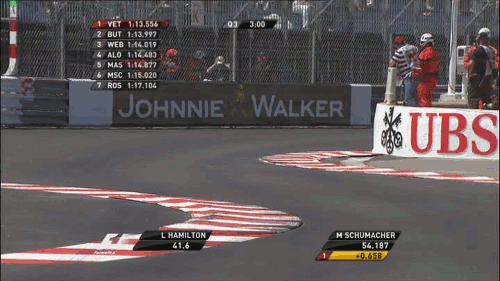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一個用槍指着德國的對手
雖然從傳統角度來說,我們是美國的盟友。可是在特朗普時代,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當下不是我們面臨貿易戰爆發的危險問題,我們實際上已經身處貿易戰之中了。美國首先對鋼鐵和鋁製品加征了關稅,歐盟與中國的反制措施類似,都對威士忌和哈雷戴維森摩托車等共和黨控制的州的產品加征了關稅。
對於德國政治家以及那些德國跨國公司來說,當下的形勢非常棘手。我們看得很清楚,美國是在挑釁,而德國並不想跟任何國家打貿易戰。
平心而論,在中國市場准入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等問題上,德國與美國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可是美國不僅在針對中國,美國也在拿着槍對準我們德國,所以德美聯合起來就上述問題與中國展開談判的可能性很小。
我們相信WTO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場所,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正在系統性地削弱所有國際機構和國際條約的權威性和影響力。WTO仲裁法庭已經患上了機能失調症,特朗普政府一年前阻撓了WTO對三位仲裁法庭法官的提名,這個問題至今都無法繼續向前推進。
美國撕毀了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了伊朗核協議、威脅退出北約、在很多問題上欺壓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這一切讓很多德國人開始思考應該到別處去尋找盟友。美國(尤其是共和黨)一貫是擁護“自由貿易”的,然而他們現在卻在系統性地破壞全球化進程。
特朗普在德國的口碑很差,即便在初選階段,我們也已經開始感覺到特朗普是個問題候選人,覺得也許只有美國人才會喜歡這樣的人物。德國人覺得特朗普當選是絕無可能的。如果讓德國人投票,特朗普只能得到15%的支持率,希拉里則可以獲得85%的選票——85%的德國人之所以願意投票給希拉里,並非因為大家多麼喜歡她,而是因為他們都很討厭特朗普,討厭他的競選團隊和競選綱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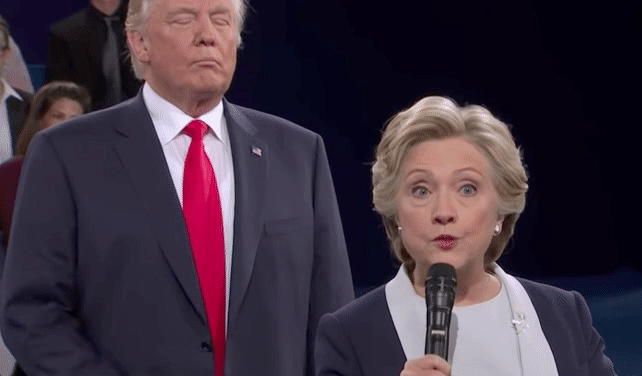
鑒於德國曾經不甚光彩的歷史,我們對極右翼勢力的發展非常警惕。那些喜歡特朗普的德國人大部分都是德國國內極右翼勢力的支持者,他們大肆宣揚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主張德國應退出歐盟和歐元區)和白人至上主義,反對移民進入德國。
大多數德國人都認為已經不可能與特朗普政府再達成任何真正的協議,因為一旦特朗普發現撕毀協議對自己有好處,他就會毫不遲疑地將其撕毀。特朗普在德國人眼中不過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衝動的、短視的、只看表面現象的膚淺政客。
大多數德國人認為德國應該更加依靠自己的實力並保持低調。一些人希望德國能有所作為,不過大多數德國人還是認為歐洲作為一個整體時說話才更有力量。我認識的許多德國人都主張德國應加強與中、俄、印等國家的關係,不過在德國國內針對這一主張仍有許多不同看法。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讓很多德國公司在美國變得十分小心。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不確定性都是一劑毒藥。德國美國商會(AmCham)在最近的一項問卷調查中發現,只有8%的德國企業認為美國的政策是可以信賴的。而在德國最大的30家公司中,有16家在美國的營業額要高於在德國的營業額。
德國已經接收到了足夠的信號,我們已經遇到了麻煩,我們必須拿出解決方案了。誰會願意在一個政策變化無常的國家投資呢?大多數德國公司的做法都意在拖延時間、保持低調,他們希望2020年美國大選能給形勢帶來一些變化。
德國媒體喜歡使用外交語言,他們總是警告說目前的形勢有升級到貿易戰的潛在危險。然而客觀地說,我們已經暴露在貿易戰的戰場上了。德國怎麼會願意與一個用槍指着自己的對手談判呢?而且這個用槍指着德國的國家還是我們的傳統盟友。
誠然,德國與美國之間曾有持續幾十年的良好關係。只是在與美國友人的幾次交談中(我曾在美國生活過兩年,期間結交了不少朋友),我才意識到,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美國只代表一半甚至一小部分美國人。希望我們不會忘記還有另一半的美國人,但是如果發聲者一直是如今的“美國”,有此“盟友”還需要什麼敵人呢?































































































